吕国英与他的哲慧诗章
——吕国英与他的哲慧诗章
赵树忠
2020年12月23日,我写了一首小诗,名字叫《致吕国英兄长》——
“阿弥陀佛/碰着您太好了/由于宿世的缘分/现代我们相遇/在我最坚苦的时辰/您自告奋勇/打扫我头上的乌云/给我阳光/您不只是兄长/照旧菩萨/布满伶俐/尊贵而巨大”

吕国英著《“气墨灵象”艺术论》
我把这首诗打印出来,挂在写字桌前,天天一昂首就能望见它。望见它,我就想起吕国英这个我生掷中的朱紫。国英兄大我两岁,我们体会于上世纪九十年月。其时,天津日报组织了一场陈诉文学作者研讨会,我和国英兄都介入了。当时国英兄在解放军天津戒备区272医院事变,时代写了大量的陈诉文学、纪实文学作品,有多篇颁发在《南边周末》《陈诉文学》《天津日报》上。谁人时辰的《南边周末》刊行量庞大,读者甚众,影响好生了得,国英兄也因此名声远播。在那次陈诉文学研讨会上,我和国英兄一见依旧,往后我们常常接洽,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自从他调到解放军报社之后,由于离得远了,也怕影响他的事变,我们的接洽比早年少了。可是一有难事、大事,我第一个想到的照旧他。在我的眼里,就没有国英兄办不成的工作、办理不了的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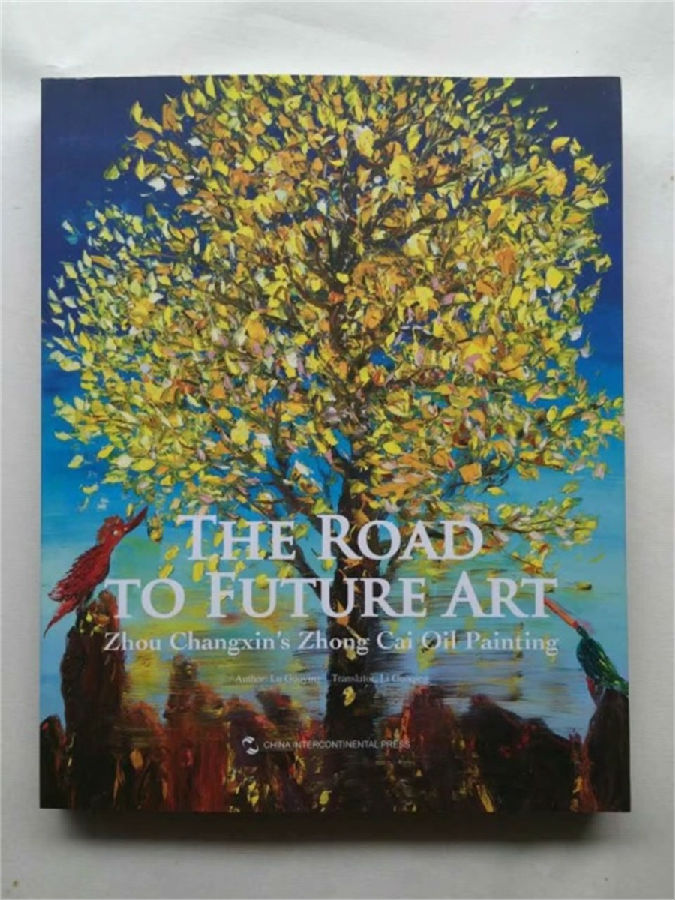
吕国英著《将来艺术之路》(英文版)
1994年,我在天津日报上颁发了一篇陈诉文学《鬼难拿》。这篇陈诉文学给我带来了庞大的贫困。由于我在这篇文章里没有点名地品评了其时的一位塘沽区的率领,这位率领对号入座,对我开始冲击反扑。在这位率领的授意下,塘沽区委宣传部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驳陈诉文学鬼难拿》,上报天津市委宣传部。几位区委常委找我发言,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说一句,率领记一句,空气异常求助。很多熟悉我的人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顶得住。这个时辰,我想起了国英兄。于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把环境具体地先容了一遍。国英兄听后对我说:“树忠,不消怕!弘扬真善美、高吭正气歌,可喜、可贺、可嘉!”又说:“应该让更多的媒体、读者知道,天津有个‘鬼难拿’,出了个发掘宣传‘鬼难拿’而被出格‘拿捏’的咄咄怪事。”很快,北京的几家消息单元到塘沽采访此事,为我主持公平。几个回合下来,对方败下阵来,找我息争。假如不是国英兄的互助,这一次我必然是凶多吉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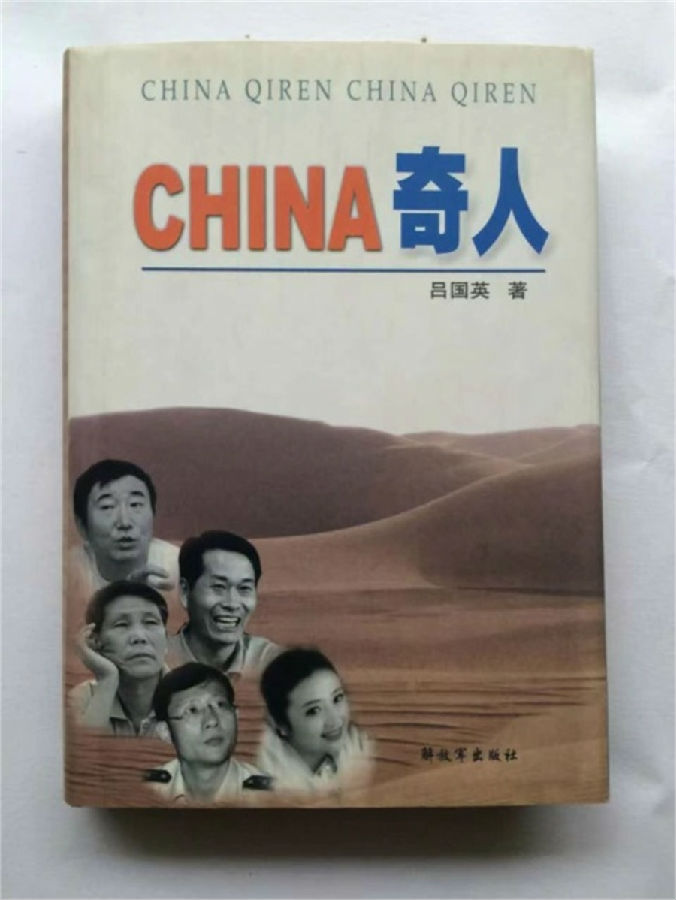
吕国英著《CHINA怪杰》
接下来的二十几年里,国英兄的奇迹风生水起,写了大量的新有名篇、重头评述、原创学术文章,出书了多部消息、纪实、艺术评述专著,在多个率领岗亭任职。令我出格信服的是,他在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岗亭上,积多年的采访调研、思索探讨,完成了原创艺术论——《“气墨灵象”艺术论》的撰写、出书,成绩了一部全新的文艺理论专著。在这部专著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艺术家给以很高评价,称这部专著站在今世美学前沿,思索人类美学、艺术学题目,传承传统美学精力,开辟新的美学认知,缔造新的美学领域,是一部居高临下的艺术理论专著,是一项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成就,对认知文艺演进诸象,构建艺术审美新理念,攀登艺术创作新岑岭,理论上矗高度,实践上眺至远。国英兄恒久致力于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化史、头脑史学研探讨,不只创建“‘气墨灵象’论”,构建文艺理论新系统;建构“‘书象’论”,提出“书象”审美新命题;还撰写《国粹千载“牛”纵横》、《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塑形立象“牛文化”,受到学界及国表里读者存眷,成为知名的文艺品评家、文化学者。
国英兄以他乘愿而来、不负义务的赤子继续,以原创、敏锐、攀登、逾越的缔造思想,不绝攀缘文化艺术学研岑岭,展示了一个军旅学人的宏伟气派和奇异魅力。

吕国英著《陶艺狂人》
尤其令我感想不行思议的是,国英兄于追学求问、撰论修真中,还涵养成为审美高格、独占认知、自成一体的狂草书家。他崇尚文墨一体、艺术原创,誊写内容皆自撰诗句。险些于狂草创作同时起,开始哲慧诗歌创作。于奇思妙想、捉灵捕慧中,写出了上千首四处赞颂的哲理小诗,其哲思、灵慧、高远、浑朴、美润、联想、感怀的审美地步,令人醍醐灌顶、精力升华。这些诗歌均为古体今用、旧章新篇、期间语句,多以五言哲思酝句、追疑问穷,又有三言、四言、六言、七言美润成章、高维化境。
2022年年头,我们加了微信,看到他在微信中的诗作。说内心话,比起他的不太好懂的艺术理论、认不太清晰的狂草誊写,我更喜好他的这些诗歌作品。这些诗作布满灵性、伶俐,悦耳肺腑,如统一股清泉,渐渐地跳跃着流进内心,让人舒服无比。我一口吻读完这些诗歌,固然里边大量的典故不甚清晰,但我能朦昏黄胧地领会到国英兄的心境。我太喜好它们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读这些诗的时辰,就似乎在读某一部西方墨客写的预言诗,那种韵味真是美好无比。
“生而倒计时,此在秒存在。问穷天地人,空寂道何奈。人文千载惑,前说岂足盖?疑哲追灵归,幻科探隐外。量子即意识,运命或可逮。”

吕国英著《大艺立三极》
这是我看的国英兄写的第一首诗。这首诗一下子把我从物欲横流的实际天下带到了虚无缥缈的精力天下。时刻固然已往了几千年,但人类面对的根基题目依然没有改变:我是谁?我从那边来?我到那边去?先人对人生和天下的熟悉真的是对的吗?一小我私人的运气是天赋定好的吗?莫非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吗?人间间真的有因果报应、六道循环吗?这首诗让我发生了很多的题目,关于本身、关于人生、关于天下、关于宇宙。我在想,这样布满空灵的诗句,必然长短常干净的人写得出来的。他暂且挣脱了人间的缠绕,健忘了名闻利养。他的意识漂流在虚空里,没有任何的障碍、约束。他仿佛还活在这个天下里,又仿佛已经往生到了另一个天下。这首诗的意境之妙,让人不行测度。
